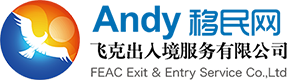點擊率:3268
澳洲人對待中國投資的態度會體現種族歧視嗎?我經常被問及這個問題,但卻很難給出答案。
2014年羅伊研究院發起的民意投票表明,56%的澳洲人認為政府接納的中國投資過多。
但澳大利亞數據署的數據則顯示2014年中國僅占澳洲海外直接投資占股的4.4%而已,美國所占股份比中國的五倍還要多。
在特定的經濟領域,比如房地產,持政府接納過多中國投資這一觀點的澳洲人比例上升至70%。負責篩選海外購房的外商投資審查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數據顯示,中國人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于2013-2014年度才開始 超越其他國家。
澳洲人對中國投資持這種態度,有一種觀點將之解釋為種族歧視,但事實并非這么簡單。像2014年羅伊投票這樣的民意投票所問的“你覺得澳洲政府允許了過多的中國投資嗎?”這類問題是根本不能說明種族歧視或其他什么問題的。
這有可能是因為澳洲人單純不喜歡外商所有權而已,不管資金來源國是哪國。又或者其實他們不在乎錢從哪兒來,可能更擔心的是外商投資的其他什么特性。
比如說,公眾可能根本不會在乎中國投資者控股本土公司,只要澳洲人還是負責公司日常運營。的確,會計事務所畢馬威(KPMG)和悉尼大學研究發現,已有證據證實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在采用這種本地化策略。
2014年的羅伊投票發現澳洲人對外商在某些特定資產上的投資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與制造業上外商投資58%的支持率相比,僅有37%的澳洲人支持外商對港口和機場進行投資。
近年來,國外投資者已在包括布里斯班(2010)、紐卡斯爾(2014)和達爾文(2015)在內的許多澳洲港口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租賃權,運營著港口。澳洲最繁忙的港口,墨爾本港的租賃權也預計于今年晚些時候售出。
我所參與的一項新研究能解釋到這個問題。這項研究所探尋的具體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公眾對于外商在評論性的澳洲基建資產如海事港口方面的投資有所傾向呢?
我們選取了1000名澳洲人作為代表性樣本,要求他們對假想中的外商投資情境進行評價,并選擇他們最歡迎的和最不歡迎的。這些投資情境涵蓋了八種不同投資特性,比如,投資后的外商控股,投資來源國,及進行投資的國外公司是國營還是私營,等等。
每個投資情境的特性都會有不同設定——一個情境可能以中國投資為特性,另一個則可能是美國——我們可以由此判斷哪種傾向因素在起作用。
研究發現他們的最大擔憂是在于外商的所有權及其控制力,而不是外資來源國。這其實是個好消息:如果種族歧視有影響的話,我們應該會看到外資來源國作為主要因素。
最讓澳洲人在意的是投資之后的外商所控股份。相比高比例的外商股份而言,大家還是喜歡外商控股低一點。大家也會更傾向簽訂短期租約,而不是長期租約。
即便如此,在參與者傾向調查中,對資金來源國的考量還是排在第三位。五個被納入考量的國家是:中國、印度、日本、阿聯酋以及美國。美國投資是最受歡迎的,而中國投資最不受歡迎。
不過,在硬要將之解釋為這印證了種族歧視仍在發揮影響之前,還需謹記三點。
第一,日本的投資也在數據上顯示出比中國投資更受歡迎,而印度投資則沒有。一方面美國與日本投資有所關聯,而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有所關聯,這其中的作用因素顯然不會是種族。
相反,中國和印度的共同點是,二者對澳洲來說都是外商投資的新來者。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現在看到的針對中國投資的態度與公眾在1960年代針對美國投資和1980年代針對日本投資的反對態度并無區別。
第二,研究顯示澳洲人更擔憂外商控股的規模,而不是外資來源國。建模結果顯示,在租約期長度等其他屬性相同的情況,公眾其實反而會更歡迎控股64%的中國投資,而不是100%外商獨資的美國。
最后,就算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投資確實沒有其他國家投資那么受大眾歡迎,種族就是唯一可能起到作用的因素。比如,如果澳洲公眾認為中國共產黨過多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話,他們可能確實會對中國投資持更為保守的態度。
換句話說,反對中國投資可能更多地與政治因素有關,而非種族因素。若要理解導致中國投資不受歡迎的各種因素孰輕孰重,尚需進一步研究。
當然,下次我再被問到澳洲人對中國投資的態度是不是有種族歧視時,我會更自信地回答,種族并非他們的主要考量。
(作者:詹姆斯·勞倫森(James Laurenceson), 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協會(ACRI)副主任兼教授)